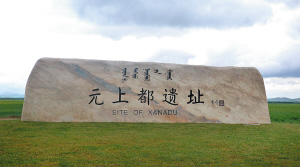天蒼蒼 野茫茫 低調申遺別嚷嚷(圖)
元上都遺址最被看重的價值是這座城承載的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當年的草原上,這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每年有半年的時間人聲鼎沸,最多時有11萬人口,《元史》里稱之為“北方巨鎮”,而在西方文學中,“Xanadu”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詞匯,泛指“世外桃源”,一譯為“仙都”,原型正是元上都。
元上都申遺成功后,會否變身為旅游熱都?查查中國眾多世界遺產的賬本,會發現許多對比強烈的數字,這些數字是激動人心的經濟效益,也是憂心忡忡的遺產未來。令人欣慰的是,在元上都未來的規劃里,明確日接待游客不超過1萬人次,至少目前,草原兒女還沒有計劃把它打造成旅游業的“自動提款機”。
歷經16年才獲準加入,元上都的申遺路讓人覺得分外漫長,但申遺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們都覺得,這個進度挺正常,甚至還比預想的早了點。
申遺工作的進度早已作出明確安排,在第一批預備清單里的五十多個項目中,元上都遺址排在第二十多名,按最初的計劃,元上都遺址將在2020年申遺。“我們都管第一批預備清單的項目稱為"第一集團",據我所知,第一集團里還有一些"老運動員"在排隊呢。后來從2020年一下子提前到2013年,又提前到2012年,弄得我們還挺措手不及的,好多工作都還沒完成,元上都遺址博物館還沒蓋起來,我們的人才隊伍也沒建立起來,電腦建模沒完成,就連元上都的歷史也還沒有完全搞清楚。”王大方說。
所謂慢工出細活,申遺辦公室為元上都遺址做的各項準備工作令世界遺產大會的官員都嘆服。
每一項世界遺產的申報都需要為之制定地方性法規或規范性文件,以確保對遺址的保護并非空談,這些規范不僅涉及遺址本身,還有眾多與遺址相關的領域。“我們制定了《元上都遺址保護管理辦法》,還針對草原、水資源、大氣、城市建設規劃等方面一共制定了20多項規范和辦法。”世界遺產大會要求不但有法律法規,還要有執行部門和監督機構,氣象站、水文站、消防隊、文物局、博物館、監控中心等一些部門也都被重新整合。“后來一位世界遺產大會的官員來元上都考察,他是韓國人,夸獎我們的工作做得真是太細致了。”
曬賬單驚四座 少說話多辦事
元上都申遺花了多少錢?這是申遺成功后,外界關心的問題之一,答案是:不到1個億。“直接給我們的撥款總和不到1個億,間接投資加在一起也不超過10個億。”王大方說。
16年才花不到1個億,平均每年的經費只有幾百萬,而國內很多世界遺產項目在申遺成功前就已經砸進去幾個億,甚至不惜舉債,堪稱“豪賭”。
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申遺,9年花了8個億,而被稱為“史上最牛申遺”的湖南崀山申遺總投資則超過10億元。這些一擲千金的項目中,相當一部分經費被用于宣傳推廣,世界遺產的名頭還沒有落實,申報項目就已天下聞名,像元上都這么“死心眼”地悶頭干活不知推廣,不但讓自己顯得勢單力薄,還白白放過了大筆旅游收入,可王大方說,正是看到了前車之鑒,元上都的申遺工作才一直保持低調。"天地之中"第一次申遺被否決了,后來再次申遺才成功,當時因為宣傳得太廣,一旦受挫壓力巨大,還有些類似宣傳很猛的項目,工作人員的壓力也都特別大,我們不想搞成那樣,不想在成功前引起太多關注。我們申遺時有規定,嚴禁說"志在必得"、"馬到成功"這種話。還有就是我們也實在顧不上宣傳了,活兒實在太多了。”王大方說。
元上都究竟告訴我們什么
現在在元上都遺址,游客能看到的都是斷瓦殘垣,而在當時,這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街市繁榮,云集各國商人,還有世界各地的旅行家。
1260年,忽必烈建元上都于內蒙古正藍旗草原,1264年,元大都建于北京,自此元朝開始了兩都巡幸制,元上都為夏都,元朝的統治者一年中會有近半年時間待在上都,一般是從4月待到9月。忽必烈來得要早一些,過了正月十五就會起程前往上都。
元上都的存在滿足了蒙古族民族大聚會的需要,元朝的統治者來到這里后會召開那達慕大會,喝酒、賽馬,好不暢快,而每當元朝統治者到來時,整座城市也開始聚攏人氣,在當時,元上都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不但有中國人,還有不少外國人。“我們對元上都遺址附近的墓地進行發掘時發現了大量阿拉伯人的墓葬,還有很多歐羅巴人,也就是白種人,但具體屬于哪個國家還有待考證,這些人都被埋在公共墓地,從墓葬規格來看并不是什么達官貴人,就是普通的公民。”王大方說。
每年,元上都需要一百萬擔糧食的供給,考古隊員在遺址里找到了小米和麥子的遺存,王大方推測肯定還有大米。“光喝奶吃肉肯定是不行的,糧食必不可少。當時將糧食賣到這里可以賣高價,而且能得到貴金屬和鹽作為獎勵,我推斷糧食應該來自江浙和兩廣,漕運到北京什剎海,然后送到元上都。”
繁榮的經濟和多種文化的融合為元上都留下了寶貴的歷史遺存,農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在這里完美結合,農耕文化不僅是中原地區漢族的農耕文化,還有阿拉伯地區和西方的農耕文化,此外,來自世界各國的公民帶來了各自的文化,猶太教、佛教、基督教等多種宗教以及漢族的龍文化,蒙古族的馬背文化都在這里繁榮并存,數百年后,文化多樣性成為了元上都申遺的核心價值。
旅游開發 還得悠著來
現在,元上都遺址的旅游已正式開放,一場新的利益權衡擺在“仙都”面前。
有了“世界文化遺產”這個招牌,旅游業收入井噴是完全有可能的。1997年,平遙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1998年門票收入從以往的18萬元升至500多萬元,麗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后,旅游綜合收入已達13.44億元。
國內很多世界遺產都拜倒在這誘人的經濟數字面前,至少那不菲的宣傳費是要先賺回來的,大興土木,建豪華酒店、娛樂設施已成慣例,吸引更多的游客來世界遺產花更多的錢。被這么一番折騰的世界遺產比受“保護”以前還危急了。世界自然遺產“三江并流”被世界遺產委員會警告,故宮、麗江古城、西藏布達拉宮被要求整頓,張家界武陵源景區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嚴肅批評。
對于元上都來說,這些都是前車之鑒。“每屆大會上,世界遺產委員會都要提出一些瀕危遺產,并進行討論,泰山就被列入過瀕危狀態,因為建了很多賓館,又有纜車,山下也有豪華建設。世界遺產大會會先"黃牌警告",如果還一意孤行,就會被清理出世界遺產名錄,去年一個德國的遺址就被清出了名錄。”王大方說。
去年,內蒙古的年游客接待量為兩千萬人次,元上都遺址的游客數為40萬人次,所占份額很小,而在申遺旅游規劃中,元上都遺址將日最大接待量控制在1萬人次,某一宮殿區最多不超過4000人,參照這一標準,遺址也沒有做大規模建設的計劃,建設越少,破壞越小。 “馬可·波羅在游記中描述元上都有可以容納幾千人的大帳篷,我們打算復建這個帳篷,設計鳥巢的團隊在負責這件事。但這里不會有馬隊或者射獵表演,這是遺產保護不允許的,或許會在其他地方搞。”王大方說。
雖然不在乎游客數量,但元上都卻很在乎對這里的評價。“來元上都參觀需要做個文化預熱,通過講解初步了解元上都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這畢竟是一個考古遺址,不做準備到來之后看到的都是斷瓦殘垣,很難體會到遺址的價值和歷史感。”王大方說。同時,元上都遺址面積太大,位于空曠地帶,對于旅游服務水平是不小的考驗。
如今在元上都遺址附近還生活著一些牧民,被稱為原住民。他們沿襲著的“祭敖包”等風俗是昔日元上都活生生的生活場景,因為他們的存在,使得元上都至今依然是一座會呼吸的城市。
申請世界遺產的其中一項是需要聽取遺產相關利益群體的意見,牧民們告訴世界遺產大會的官員們,游客多了,奶豆腐就好賣,能多賺點錢。上都牌白酒在申遺成功后忽然變得熱銷了,但一瓶只賣幾十塊錢。
元上都申遺辦公室提供圖片
編輯:dongjing
相關閱讀
評論:商業和利益裹脅世界遺產的救贖之道
商業和利益裹脅世界遺產的救贖之道在哪里?新聞說的好,“監督機制固然重要,如何讓其行之有效仍需做更多考量,關鍵是我們何時能擺脫經濟利益的枷鎖,只將保護文明當作一次朝圣。” 【詳細】
揭秘元上都遺址成功“申遺”經驗
北京時間6月29日深夜,從俄羅斯圣彼得堡召開的第36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傳來喜訊――我國申報的元上都遺址經大會審議,一致同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我國第30處世界文化遺產宣告誕生。【詳細】
內蒙古元上都遺址景區廣場工程竣工
記者昨日從正藍旗旗委宣傳部了解到,元上都遺址景區廣場工程日前正式竣工。【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