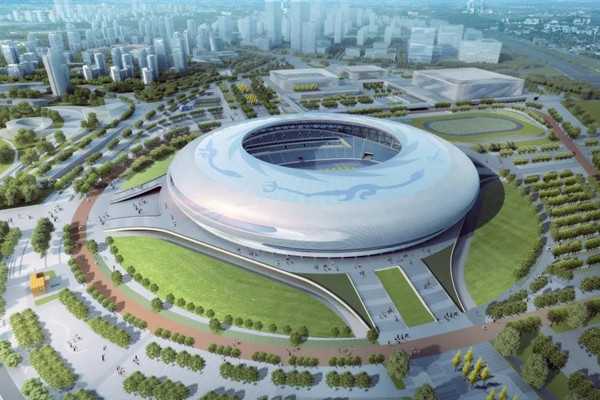中國城鎮化正處于重大轉型期
總體上講,結構效率、規模效率和分工效率是城市化驅動經濟增長的三條渠道,如果不具其一,那么城市化就幾乎不可能會伴隨經濟增長。通常,在城市化的早期階段,結構效率居于主導地位,恰當的政策應該是促進人口自由流動,使農業勞動力最大限度地轉移至非農產業,從而促成生產率的提升。然而,隨著城市化進入中后期階段,即城市人口增長速度趨緩,甚至不再增長,規模效率和分工效率開始居于主導地位,此時,恰當的政策應該是在促進人口聚集效應所發揮的規模和協同作用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消除人口密度過高所產生的負作用。
1880—1940年的61年間,美國的城市化率與人均GDP增長率保持了極為一致的相關性,然而1940年之后,美國的城市化率超過60%之后,城市化速度明顯放緩,但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依然保持上升態勢。一般性的解釋是,在初始階段,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強相關性反映的是勞動力等資源從農業向工商業轉移帶來生產率上升,這是一種資源的產業配置效應;而在城市化的中后期,收入的上升反映的則是工業和服務業內部生產率的大幅度改進,而這通常是由技術進步、知識溢出和規模經濟效應所引起。一個相反的案例是巴西,20世紀60年代后期,巴西的城市化率為50%,在其后的20年里,伴隨著城市化的繼續推進,生產率與人均收入也有明顯的上升,但80年代之后,雖然城市化率仍在上升,但人均GDP水平卻一直止步不前,甚至在1980年之后的5年里連續出現大幅度下降。
過去10多年,中國在將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效率更高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由2001年的50%下降到2011年的35%,這11年間,中國的城市就業增長率平均每年為3.3%,11年累計創造了近1.5億個就業崗位,城市就業總量增長了40%。由于農業勞動者的生產率僅是城市勞動者的10%左右,這種大規模的就業轉換促進了中國生產率的大幅提高,這也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之一。
然而,相對于結構效率的快速提升,中國規模效率和分工效率的提升并不顯著。從過去10多年的經驗來看,這兩種效率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例如即使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其人口規模和人均收入之間似乎也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另外,由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生產中心集中在東部沿海,中國發揮的是制造業中心的作用,真正與中國制造業形成分工的是海外服務業,例如中國產品出口到海外,使用的是海外的供應鏈體系。因此,中國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分工效率并不明顯。
展望未來,中國的分工效率和規模效率的提升潛力巨大,也只有這兩種效率逐步提高,才能對沖結構效率自然下降帶來的效率損失。具體而言:其一,從區域之間的分工來看,沿海城市由于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制造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但是內陸地區,特別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率很高的河南、江西和廣西,現在的人口紅利依然存在,且較為顯著,勞動力成本仍低于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亞洲經濟體,這吸引制造商從中國沿海遷至內陸地區。原則上,這可以說是一種跨區域的制造業重新配置,也是一種對沖沿海成本上升和實現區域間產業分工的必然選擇。其二,從城市之間的分工來看,內陸中心城市在未來的制造業發展浪潮中通常是作為中高端科技型產業的中心,中低端制造業為了規避高地價和高房價,往往傾向于選擇內陸中小城市,使之成為生產和制造中心,從而形成中心—外圍城市、中心城區—郊區之間的制造業分工。其三,從規模效率來看,未來若能形成以城市群為載體的空間結構,沿海和內陸中心城市的人口聚集、知識溢出和勞動力匹配等方面的規模效應也將逐步顯現。
然而,分工效率和規模效率的實現也需要中國未來的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的政策作出必要的改變:其一是加大對沿海與內陸之間交通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和融資支持力度,將內陸城市與沿海城市連成一體,承接產業轉移;其二是加大對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化設施的投資和融資支持力度,通過城際公交、城際鐵路、城際客運、支線機場軌道交通將城市與郊區、中心與外圍連成一體,降低生產和貿易成本;其三是治理“城市病”,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人口聚集所產生的負外部性,從而將經濟集聚的正外部性保持在較高水平。
第二個命題:中國未來城鎮化的核心內容在于人口城鎮化的轉型
愛德華·格萊澤在其著作《城市的勝利》中曾精辟地指出:“城市實際上是一個彼此相互關聯的人類群體,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人。”在我們看來,人是產業和城市互動融合的核心,有“產”才有“城”,產業是城市的基礎,是城市財富增長的源泉,有競爭力的產業塑造可持續增長的城市;有“人”才有“產”,通常,人口的持續凈流入是判斷一個城市產業增長潛力的關鍵指標,更為重要的是,人口素質和人口結構對于城市經濟增長的持續性也同樣重要,一個擁有更多年輕人才的城市,必然更充滿經濟活力。
從這個角度看,人口的城鎮化作為城鎮化有機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對于中國而言,無論是同發達國家,還是同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人口城鎮化的含義都要遠為復雜。具體而言:
第一,從正常邏輯來看,城鎮化進程中按人口流動主導方向可分為四個階段:從農村進入城市、從小城鎮進入大城鎮、從城區進入郊區、郊區城鎮化從而形成大都市圈。因此,不同階段的人口流向并不相同,人口城鎮化的含義也自然不同。以美國經驗來看,1920年之后,美國城市化率突破50%,人口城市化率上升的速度趨緩。1970年,美國大都市區內,郊區人口數量超過了中心城市人口數量,郊區成為中產階級的天下,經濟重心也隨之轉移到那里,汽車文化大行其道,郊區的購物城取代了市中心商業區,成為零售業的主導形式。1979年,美國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0%,之后,基本保持穩定,但人口集中的趨勢沒有變,只是城市的空間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周邊的郊區也被囊括其中,構成以多中心為主要特征的大都市區。1990年,又是一個劃時代的年份,美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居民人口超過100萬的大型都市區里,美國的都市區化又向大型化邁進了一步。從此,城市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城鄉概念已不能準確描述美國的人口分布,取而代之的是大都市區和非大都市區。
從中國的情況看,2011年,城鎮化率突破50%,作為一個標志性轉折點,未來人口流向很可能會發生多層次的變化。在這個臨界點之前,人口的主導流向是從農村進入城市,尤其是進入大城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外來人口1.4億人,其中80%集中于上海、深圳、北京、東莞、廣州等50個城市,外來人口數量排名前十的城市的人口流入占比就高達43.2%。在此之后,人口的流向將從單一逐步走向多元:其一,鑒于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仍處于較低水平,農村仍然存在一定規模的勞動力,未來若能順利推動農業規模種植和農業工業化,農村仍有可能節約出不少勞動力,他們仍將繼續沿著從農村到城市的傳統道路遷移。其二,鑒于沿海及個別發達城市生活成本日益提升,且伴隨著流動人口的老齡化和工業崗位的內遷,未來將有部分流動人口返回內陸,甚至返回家鄉。其三,隨著交通一體化,中心城市和郊區之間的產業分工將發生變化,人口的重新分布也將是自然趨勢。
第二,從城鎮存量人口的分布結構看,盡管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突破50%,在6.9億城鎮常住人口中,卻只有60%左右居住在650多個城市(含直轄市、地級市和縣級市),仍有40%左右即2.8億左右的常住人口居住在近2萬個鎮區。
編輯:daiy
相關閱讀
北京首發森林體驗指數
很多森林看起來大同小異,但因風速、濕度、負氧離子濃度等的不同,游憩的感受相差很大。到底哪片森林更適合您的出游需求呢?昨天,北京首次上線森林體驗指數,為市民走進自然踏青賞花提供參考【詳細】
“十四五”期間 四川力爭建成200個體育公園
通過重點推動體育公園建設、綠道建設等場地設施建設,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銀邊建設便民利民的場地設施等手段,扎實推進健身場地設施補短板工作,完善四級全民健身設施體系,進一步滿足人民群眾15分鐘健身圈需求【詳細】
河北定州加快創建國家園林城市
定州把創建國家園林城市、籌辦河北省第七屆(定州)園林博覽會兩項工作做為彰顯特色、打造品牌的重要路徑,做為提升文化、惠及民生的重要載體,圍繞城市框架拉伸、文旅產業發展、人居環境提升、新興產業布局做文章【詳細】
探營廣州園博會:移步換景賞雅色 繡球簇擁廣州城
第30屆廣州園林博覽會將于3月24日至4月2日舉行,3月22日,記者提前探營廣州園博會多個會場花境,發現富有傳統和現代元素的造景、包含多個區域特色的小園圃等已逐漸展露真容【詳細】